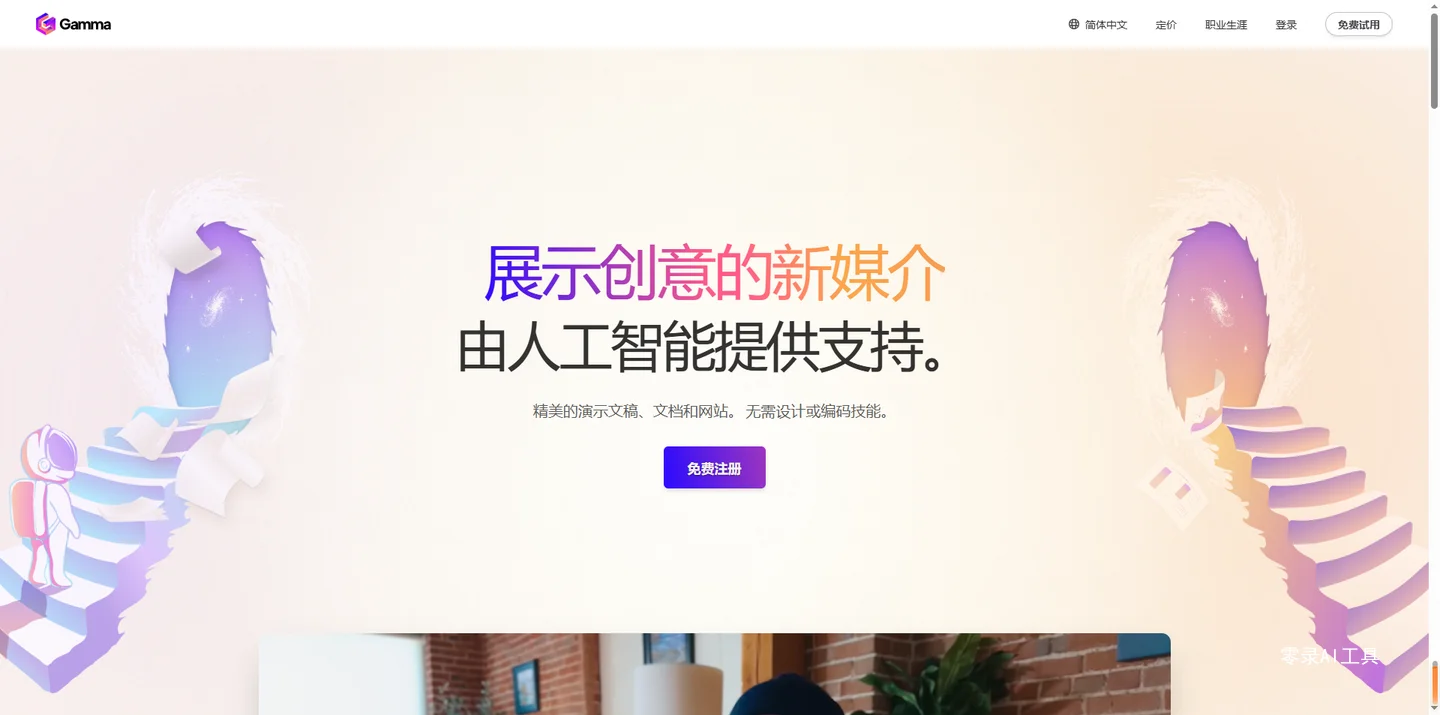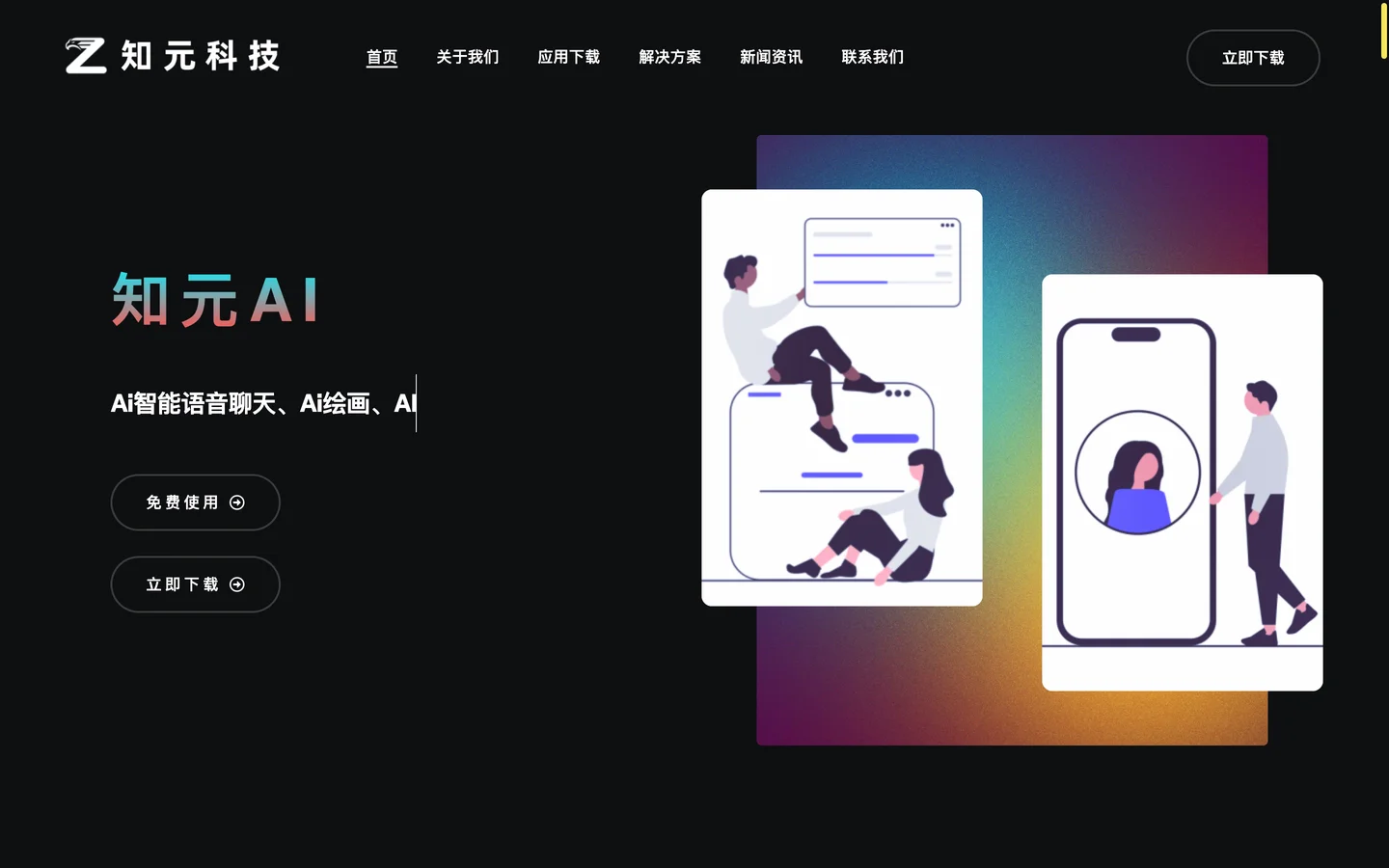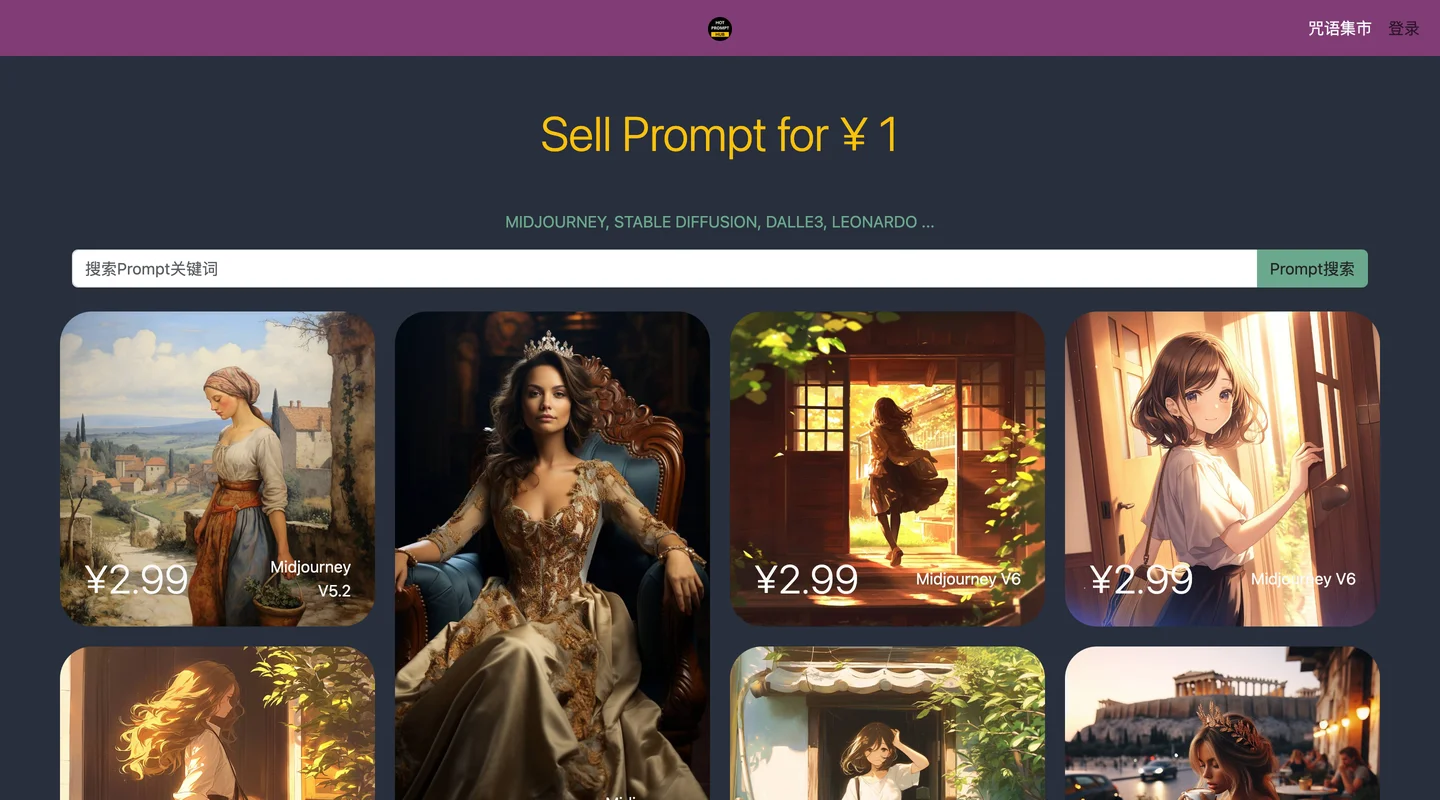翻译:韩杨
有了地形学的记忆,人们可以谈论一代代人的视觉,甚至可以谈论一代代人的视觉遗传。与此相反,知觉的逻辑及其使几何学非地方化的新载体的出现,带来了一种视觉优生学,一种对精神意象多样性的先发制人的颠覆,一种对注定不存在的意象群体的先发制人的颠覆。
1.重组一个被肢解的上帝
来自古代吠陀的关于宇宙形成的迷人神话,据说古神生主在创造宇宙的过程中被粉碎。当世界诞生时,至高无上的上帝被发现被肢解,被毁灭。与他的火祭坛仪式中,印度教信徒象征性地重组神的破碎身体,他们根据精心设计的几何图案建造了一座火祭坛。2火祭坛是由成千上万块形状和大小精确的砖块排列而成,形成了一只猎鹰的形状。他们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将每块砖准确地放入指定的编号和位置,并且在铺设过程中他们还口诵咒语。解决逻辑谜题的关键是仪式,每一层都必须保持相同的形状和相邻的区域,但砖块的位置却不同。最后,猎鹰祭坛必须面向东方,这是重建后的上帝象征性地向着升起的太阳飞行的前奏——一个用几何方法来表现神性化身的例子。
插图来自Frits Staal,“希腊和吠陀几何学”,印度哲学期刊27.1(1999):105-127。
创作于约公元前800年印度的《苏尔巴经》(《Shulba Sutras》)中描述了火坛祭仪式,记录了一个更古老的印度传统。《苏尔巴经》(《Shulba Sutras》)讲述了建造特定几何形状的祭坛,以确保贡献给神的礼物:例如,书中说:“那些希望摧毁现存和未来敌人的人应该建造一个菱形的火坛。”3火坛祭那复杂的猎鹰形状是由七个正方形组成的示意图逐渐演化而来的。在吠陀的传统中,传说仙人的灵魂都由七个方形的神我(宇宙实体或人)组成,生主就是从这种形式出现而来。1907年,艺术史学家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提出,原始艺术诞生于洞穴涂鸦的抽象线条中,但人们可能会认为,艺术手法也是通过线条和碎片的组合而出现的,之后又引入了复杂的形式和几何的技术。4意大利数学家保罗·泽里尼(Paolo Zellini)对吠陀数学的研究中发现,火坛祭被认为是传递几何近似和增量增长的技巧——换句话说,算法技巧——可与莱布尼茨和牛顿的现代微积分相媲美。5阿格尼察耶那是印度最古老的仪式之一,至今仍在实践,是算法文化的原始例子。
但是我们如何定义一个像火坛祭这样古老的仪式为算法呢?对许多人来说,通过最新技术的范式来解读古代文化可能是一种文化挪用行为。然而,声称文摘技术知识和人工的元语言独特的属于西方现代工业,不仅是历史上不正确的行为,内隐认知的殖民主义的眼光看待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的文化的表象。6法国数学家让-卢克·夏伯特(Jean- Luc Chabert)指出,“算法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早在一个专门的词被创造出来描述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算法只是一套逐步的指令,机械地执行,以达到某种期望的结果。”7如今。有人认为算法被视为一次技术创新实现抽象的最新数学原理。算法是最古老的物质实践之一,比许多人类工具和所有现代机器都要早:
算法并不局限于数学……巴比伦人用算法来决定法律,拉丁语老师用它们来获得正确的语法,他们也用于预测未来,决定医疗、或准备食物等所有文化中也用到了算法……因此,我们说的食谱、规则、技术、流程、程序、方法等,也使用相同的词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例如,中国人在数学和武术中都使用“术”这个词(意思是规则、过程或计谋)……到现在,‘算法”这个词来表示任何系统计算的过程,即这些过程都可以自动执行。如今,主要由于计算的影响,算法一词的含义已经局限到仅仅代表一个基本要素,将其与过程、方法或技术等较模糊的概念区分开来。
在数学和几何得到巩固之前,古代文明已经是社会分割的大型机器,用抽象的概念来标记人类的身体和领土,这些抽象概念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上千年。此外,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也提出了一系列古老的抽象和社会分割技术:“纹身、切除、切割、雕刻、刻划、肢解、包围和初始化。”9数字已经成为社会分割和领土划分的“原始抽象机器”的组成部分,人类文化正是来源于此,例如;第一次有记录的人口普查发生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逻辑形式是由社会形式构成的,数字则是通过劳动和仪式、纪律和权力、标记和重复而产生的。
20世纪70年代,“民族数学”开始打破精英数学的柏拉图式循环,揭示了计算背后的历史主题。10正如黛安·纳尔逊(Diane Nelson)提醒我们的那样,当前关于计算和算法政治的辩论的核心政治问题最终非常简单;谁说了算?谁来计算?11算法和机器不会自己计算;它们总是为别人计算,为机构和市场计算,为工业和军队计算。
2.什么是算法?
“算法”一词来自于波斯学者阿尔·花拉子密(al-Khwarizmi)的名字的拉丁化。他在9世纪写于巴格达的《印度数字计算》一书中,将印度数字和相应的计算新技术——算法引入西方。事实上,中世纪的拉丁语“algorismus”指的是用印度教数字进行四种基本数学运算——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的程序和捷径。后来,术语“算法”用来比喻表示任何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并成为核心的计算逻辑。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区分算法历史上的三个阶段:在古代,算法可以认为是程序化、规则化仪式的过程,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传递规则;在中世纪,算法是一种辅助数学运算的过程;在现代,算法是一个逻辑过程,由机器和数字计算机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从火坛祭仪式和印度计算规则的传统实践中,我们可以勾画出一个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算法”的基本定义:(1)算法是一个重复抽象的过程,是对时间、空间、劳动和操作的组织:它不是一个规则是由上而来,而是从下而来的规则;(2)算法将过程划为有效的步骤,以便有效地执行和控制;(3)算法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超越局限约束的发明:任何算法都是一个技巧;(4)最重要的是,算法是一个经济的过程,它必须在空间、时间和能量上使用最少的资源,以适应有限的情况。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强大,人们倾向于将算法视为抽象数学思想在具体数据上的应用。而相反的是,算法的历史表明,它的形式来自于物质实践,来自于空间、时间、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世俗划分。仪式过程、社会惯例以及空间和时间的组织是算法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甚至在神话、宗教、尤其是语言等复杂的文化系统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就人类起源而言,可以这样说,可以理解是社会实践和仪式中的算法过程使数字和数字技术开始出现,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只要看看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现代计算正在从具体形式逐渐发展到越来越抽象的形式。
3.机器学习作为计算空间的兴起
在1957年,在位于纽约布法罗的康奈尔航空实验室,认知科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发明并建造了感知器,这是第一个可操作的人工神经网络——所有机器学习矩阵的鼻祖,当时这是一个机密军事秘密。12感知器的第一个原型是一个模拟的计算机,由一个个20x20的感光元(成为“视网膜”)的输入设备组成,通过电线连接一层人工神经元,解析到一个单一的输出(一个灯泡打开或关闭,表示0或1)。感知器记录的“视网膜”简单的形状如信件和三角形和电信号传递给大量的神经元计算结果根据阈值逻辑。感知机是一种可以被教识别特定形状的照相照相机。做出一个有误差幅度的决定(使之成为一个“智能”机器)。感知器是第一个机器学习算法,一个基本的“二进制分类器”,它可以确定一个模式是否属于一个特定的类型(输入图像是否是三角形,是否是正方形,等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感知器逐步调整其节点的值,以解决大型数值输入(四百数字的空间矩阵)到一个简单的二进制输出(0或1),感知器给结果1如果输入图像是公认的在一个特定的类(例如一个三角形);否则结果是0。最初,需要人工操作员训练感知机学习正确的答案(手动将输出节点切换到0或1),希望机器在这些监督关联的基础上,将来能够正确识别相似的形状。感知器的设计不是为了记住一个特定的模式,而是为了学习如何识别任何模式。
第一个感知器中的20×20光感受器矩阵,开启了一场无声的计算革命(在21世纪早期,随着“深度学习”(一种机器学习技术)的出现,它成为了一种霸权范式)。虽然灵感来自生物神经元,但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看,感知器标志着一个拓扑形态而非生物形态的计算转折;它标志着“计算空间”或“自计算空间”范式的兴起。从那时起,计算范式中进入了第二个空间的维度,在此之前的计算空间中只有线性维度(参见图灵机,它只能沿着线性的纸带读写0和1)。这种拓扑转变,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人工智能”的核心,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从被动信息范式到主动信息范式的转变。与用自顶向下的算法处理视觉矩阵不同(就像今天用图形软件程序编辑的任何图像一样),在感知器中,视觉矩阵的像素是根据空间配置以自底向上的方式计算的。可视化数据的空间关系决定了计算它们的算法的操作。
由于它的空间逻辑,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最初致力于神经网络被称为“计算几何学”。计算空间或自我计算空间的范式与二战后控制论的核心——自组织原则的研究有着共同的根源,比如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1948年)和康拉德·祖兹(Konrad Zuse)的《雷金德劳姆》(Rechnender Raum by, 1967)。13冯诺依曼的细胞自动机的一群像素,它们被视为小细胞一个网格,这一变化状况和根据他们的邻近细胞移动,组合几何图形,像生命形式的发展。细胞自动机已被用来模拟进化和研究生物系统的复杂性,但它们仍然是有限状态的算法,仅限于相当有限的宇宙。康拉德·祖兹(Konrad Zuse)(1938年在柏林制造了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试图将细胞自动机的逻辑扩展到物理学和整个宇宙。“rechnender Raum”(即计算空间)的概念是由离散单元组成的宇宙,这些离散单元的行为与相邻单元的行为一致。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最后一篇论文“形态形成的化学基础”(发表于1952年,在他去世前两年),也属于自计算结构的传统。14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认为生物系统中的分子,是能够解释复杂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例如水螅的触须模式,植物的轮盘排列,胚胎的原肠原肠,动物皮肤上的斑点,以及花中的叶序排列。15
冯·诺依曼(Von Neumann)的细胞自动机和康拉德·祖兹(Konrad Zuse)的计算空间和空间模型直观易于理解,而感知器神经网络显示一个更复杂的拓扑,需要更多的关注。实际上,神经网络采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组合结构,这可能使它们成为机器学习中最有效的算法。据说神经网络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根据通用近似定理(用一定数量的神经元层和计算资源)来近似任何模式的功能。机器学习的所有系统,包括支持向量机、马尔可夫链,Hopfield网络、玻耳兹曼机,和卷积神经网络,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开始计算几何的模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古老的组合学艺术的一部分。16
4.视觉劳动的自动化
即使在二十世纪末,也没有人会想到把一个卡车司机称为“认知工作者”,或者是一个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机器学习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中的应用让人们对如驾驶等手工技能有了新的理解,人们发现了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般来说,不仅仅是手工的,还有社会的和认知的(以及感性技能,劳动应当介于手工和认知之间,但人们在这方面对劳动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司机做什么工作?人工智能是否会带着它的传感器来记录,用它的统计模型来模拟,用自动化来代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看看哪些技术已经成功实现了自动化,哪些还没有。

自动化驾驶工业项目已经表明(比政治和经济更甚),驾驶劳动是一种遵循着成文法的规则和自发的社会习俗的自发性活动。但是无论如何,如果驾驶技术可以转化为一种算法,那将是因为驾驶具有逻辑推理结构。驾驶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活动,就像劳动一般来说也是合乎逻辑的活动一样。这一假设有助于解决劳动劳动与智力劳动分离这一老生常谈的争论。17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悖论,人工智能AI算法的发展使得在劳动中认识到一个长期被批判理论忽视的认知成分成为可能。劳动与逻辑的关系是什么?这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自动完成司机在繁忙的道路上必须做出的所有细微决定。它的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即模仿和复制)道路空间的视觉感知和车辆机械动作控制(转向,加速,停止)的机械动作之间的人为相关性,并以此为依据,在几毫秒出现危险时保证车内和车外的人的安全。18很明显,驾驶工作需要高认知能力,而这不是靠即兴发挥和本能就能做到的,而且,由于习惯和训练不全意识训练,快速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是可能的。驾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既遵循成文的规则(带有法律约束),也遵循自发的规则,包括任何司机都必须遵守的一种默认的“文化代码”。人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在孟买开车和在奥斯陆开车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开车是一种强烈的感知劳动。事实上,劳动在本质上都是感性的,通过在一眨眼的时间里不断进行的决策和认知。认知不能完全从空间逻辑中解脱出来,它往往遵循更为抽象的空间逻辑。观察——感知是逻辑的,认知是空间的——是经验证明的,没有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算法的大吹大擂,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算法构建模型以统计地推断视觉空间(编码为3-D道路场景的数字视频)。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中取代的司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司机,而是一个集体的工作者,一个引领城市和世界的社会大脑。19仅从自动驾驶汽车的企业项目来看,很明显,人工智能是建立在集体数据基础上的,这些数据编码了空间、时间、劳动和社会关系的集体生产。AI模仿、替换和摆脱有组织的社会空间分工(材料显示第一个算法,而不是数学公式的应用或分析抽象的)。
5. 空间的记忆和智能
保罗·维里奥(Paul Virilio)是法国的速度或“流科学”哲学家,同时也是空间和拓扑学理论家,因为他知道,技术加速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就像它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一样。有趣的是,Virilio的书《视觉机器》(The Vision Machine)的名字灵感来自感知器算法。作为二十世纪思想家的经典学识,Virilio在基于空间化的古代记忆技术(如位置法)和作为空间矩阵的现代计算机记忆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西塞罗(Cicero)和古代记忆理论家认为,通过正确的训练可以巩固自然记忆。他们发明了一种地形学系统,即轨迹法,这是一种基因座方法,由一系列地点和地点组成,这些地点和地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很容易被排序。例如,你可以想象在房子里闲逛,选择不同的桌子,从门口看到的椅子,窗台,墙上的标记。将要记住的材料编码成离散图像,并且将每个图像以适当的顺序插入到各个位置。例如,记住一个演讲的内容,你把要点转换成具体的图像,并在头脑中把每个要点按顺序排列在每个连续的基因座上。到演讲的时候,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房子的各个部分都整理好。
将空间、拓扑坐标和几何比例转换成一种记忆技术,基本上相当于将集体空间转换成一种机器智能的来源。在书的最后,Virilio对图像在感知机等“视觉机器”时代的地位进行了反思,对人工智能即将到来的“视觉工业化”时代发出了警告:
“现在,物体感知到了我,”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这一惊人的论断最近已成为客观事实,即真理。毕竟,他们不是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造一种“视觉机器”,一种不仅能够识别形状轮廓,而且能够完全解释视野的机器吗?他们不是也在讨论视觉学的新技术吗:通过计算机控制摄像机来实现失明视觉的可能性?这种技术将用于工业生产和库存控制;也许在军事机器人领域也是如此。
他们正在为感知的自动化、人工视觉的创新、将客观现实的分析委托给机器做准备,或许可以重新审视虚拟图像的本质。不要忘记感知器背后的整个理念是鼓励第五代“专家系统”的出现,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只有通过获得感知器官才能进一步丰富。
6. 结论
通过了解火坛祭的古老几何学,第一个神经网络感知器的计算矩阵,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的复杂导航系统,也许这些不同的空间逻辑结合在一起可以将算法作为一种突现形式来阐明,而不是一种技术上的先验。火坛祭仪式是一个紧急算法的例子,因为它编码了社会和仪式空间的组织。仪式的象征功能是通过世俗手段重建上帝;这种重建的实践也象征着“一”中的“多”的表达(或“一”通过“多”的“计算”)。仪式的社会功能是世代相传基本的几何技能和建造坚固的建筑物。21火坛祭仪式是一种算法思维的形式,它遵循原始的和直接的计算几何学的逻辑。
感知器也是一种经验产生的算法,它根据空间划分进行编码,具体来说就是可视数据的空间矩阵。感知器的光感受器矩阵定义了一个封闭的领域,并处理一个根据其空间关系计算数据的算法。这个算法也表现为一个由经验产生的过程——一个过程、一个模式在重复之后的编码和结晶。所有的机器学习算法都是紧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复类似的模式“教导”机器,并使模式以统计分布的形式出现。22
自动驾驶汽车是一个复杂经验产生算法的例子,因为它是从一个复杂的空间结构,即道路环境作为交通法规和自发规则的社会制度发展起来的。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在记录了这些自发的规则和给定地区的交通代码后,试图预测可能在繁忙道路上发生的意外事件。在自动驾驶汽车的例子中,自动化的企业乌托邦将人类驾驶员彻底消灭,期望道路场景的视觉空间将单独决定地图的导航方式。
火祭坛仪式、感知器和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自我计算空间和紧急算法的形式(也许,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劳动隐形化的形式)。
计算空间或自我计算空间的概念特别强调,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基于空间、时间、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世俗和物质划分的新兴系统。机器学习是从网格中产生的,网格延续了古代的抽象和仪式,这些仪式与标记领土和身体、计算人口和物品有关;这样,机器学习本质上就是从社会劳动的扩展分工中产生的。尽管人工智能经常被框定和批评,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人工”或“外来的”:在意识形态通常的神秘化过程中,它似乎是一种像古代戏剧中那样降临到世界上的“神机妙算”。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实际上来自这个世界的智慧。
人们所谓的“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将集体行为、个人数据和个人劳动结晶为私有化的算法,用于复杂任务的自动化:从驾驶到翻译,从物体识别到音乐创作。正如工业时代的机器产生于实验、技术以及熟练工人、工程师和工匠的劳动一样,人工智能的统计模型产生于集体智慧产生的数据。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集体智慧的一个巨大的模仿引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社会分工。